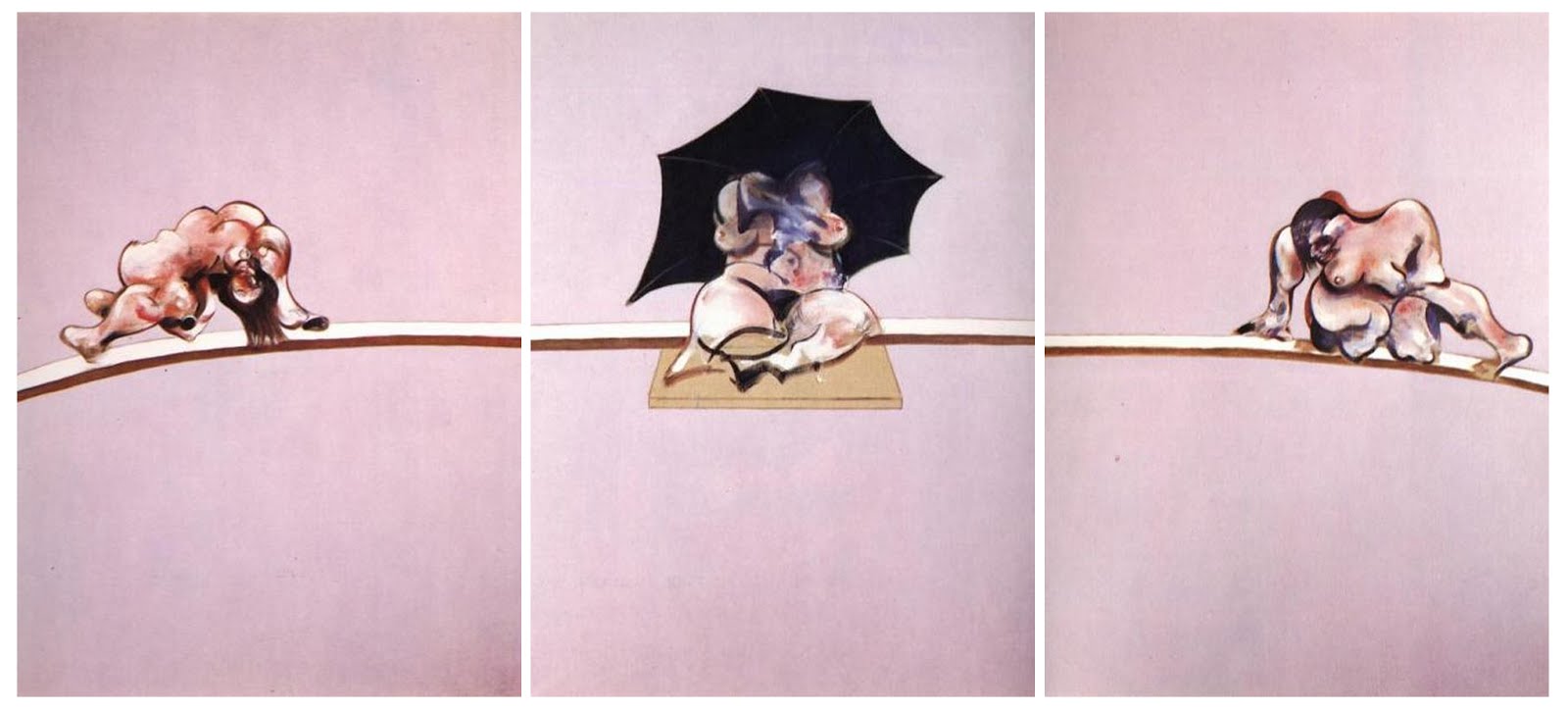Wednesday, April 1, 2015
Friday, March 20, 2015
浮雲:20 Mar. 2015
上週六,前往佩妮家做飯前,我們買了金色三麥啤酒準備帶過去。在電扶梯上,鬆獅問我:「我七月可不可以去日本?」那是日本藝術季招募志工,一個月。
我從來不認為伴侶能有拒絕另一伴往其理想去處發展的理由,所以應好。志工期七月底至九月,返台,九月再回到日本入學。就這些時光,短短的。
人對時間的知覺是這樣的:每週每多要在消防局多忙一個小時,都嫌長;然若對不捨之物的眷戀,僅賸下幾個月可以相見的辰光,都有令人措手不及的喟嘆。
帶著告別的心以相見;帶著相見的心以期告別後的未然。饒是此世間風起雲湧,饒是明日有不可預期的殘酷,關係離合千回百轉,願也有慈悲。
鬆獅有懶懶的說話方式,也因此他用著懨懨的可愛問我「可不可以」像在撒嬌。上週六我不曉得他已經把我看成男友,也因此聽到這種撒嬌高興了很久。那時傻傻的,今午窩在辦公室處裡公文,恍然興起不捨,其實那是一個月見不到他。有時不懂自己為什麼總是對這世間懷有不捨之情,以為瀟灑一點會很帥啊。
執就是人作為存有的動力。不明白這件事而談論無常者,就無法談論成住壞空裡人又何如成,住且何如住,無常自身如何無常。無明盡,亦無無名盡。
我從來不認為伴侶能有拒絕另一伴往其理想去處發展的理由,所以應好。志工期七月底至九月,返台,九月再回到日本入學。就這些時光,短短的。
人對時間的知覺是這樣的:每週每多要在消防局多忙一個小時,都嫌長;然若對不捨之物的眷戀,僅賸下幾個月可以相見的辰光,都有令人措手不及的喟嘆。
帶著告別的心以相見;帶著相見的心以期告別後的未然。饒是此世間風起雲湧,饒是明日有不可預期的殘酷,關係離合千回百轉,願也有慈悲。
鬆獅有懶懶的說話方式,也因此他用著懨懨的可愛問我「可不可以」像在撒嬌。上週六我不曉得他已經把我看成男友,也因此聽到這種撒嬌高興了很久。那時傻傻的,今午窩在辦公室處裡公文,恍然興起不捨,其實那是一個月見不到他。有時不懂自己為什麼總是對這世間懷有不捨之情,以為瀟灑一點會很帥啊。
執就是人作為存有的動力。不明白這件事而談論無常者,就無法談論成住壞空裡人又何如成,住且何如住,無常自身如何無常。無明盡,亦無無名盡。
Thursday, February 26, 2015
鬆獅:26 Fevrier 2015
J特地從政大來找我吃飯,抽幾根菸,過去揣在心上的情感把路逼仄,如今相伴走在早春的路上終於恢復坦道。人情道義是這個樣子的,雙方歷經窄途、歧路,遙指他方,而又可以安然走在一起大許就算福氣。
Wednesday, February 25, 2015
疏林:《一無所有》(未完)
「我在東南營區時,有個男人死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情形。他車子引擎出了毛病,在路上撞得飛了起來,著地後起火。大家把他救出來,但是他全身都被火燒著,是不可能生還的。他後來還活了兩個小時,可是根本沒有理由還能活那麼久。我和另外兩個女孩子在那裡陪著他,等別人從沿海地區拿麻醉藥過來。因為那裡根本沒有醫生,除了杵在那裡陪他,你也不能為他做什麼。那個人嚇壞了,意識倒是很清楚,痛得不得了,煮藥是因為他的手。我想他應該不知道他身體其他部位都燒成炭了,他只覺得雙手劇痛。你不能碰觸他好給他撫慰因為他的皮肉一定會掉下來,他一定會尖叫,根本不能給他任何幫助。也許他知道我們在那裡,我不清楚,但這對他沒有任何幫助,因為你什麼都不能做。然後我得到一個真理,那就是我們根本不能為任何人做任何事,我們不能救別人,就連救自己都沒辦法。」
「然後你還剩什麼呢?孤立與絕望!薛維克,你根本就是在否定互助關係!」高挑的女孩大聲喊。
「沒有!我沒有!我只是在說我認為的互助關係是怎樣的,它是從......從分享痛苦開始。」
「那在哪結束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還不知道。」(64-5)
「然後你還剩什麼呢?孤立與絕望!薛維克,你根本就是在否定互助關係!」高挑的女孩大聲喊。
「沒有!我沒有!我只是在說我認為的互助關係是怎樣的,它是從......從分享痛苦開始。」
「那在哪結束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還不知道。」(64-5)
Wednesday, January 28, 2015
浮雲:28 janvier 2015
一個晚上過去,日子忽然轉冷。晨間出門時天空噙著很小的雨,著小外套走在路上人就顯得像是一條薄薄的路。
想一想,我是個在生活上相當笨拙的人,常以土法煉鋼的方式過著生活。這樣的人還奢望於物質層面上好好地照顧人,下場就是會惹出許多愚蠢的事蹟。我想好好地照顧人啊,我想拋棄愚蠢的技藝,彷彿我不曾出師一樣。
每日睡前都會焦慮地如廁,深怕尿床。請保佑下鋪的男子吧,萬天神佛。
/
同梯役男讀到我電腦螢幕上,PennySaf Chiang寫:「我們辦公室的異男又在跟另一個單位的女同事聊天」,興奮地問我,可愛的佩妮(我的同梯想跟佩妮要電話)所在的工作單位也有役男嗎?
這是倒反的程序。就跟胖胖對我說,他到現在聽到別人說「役男」時,也還是無法回神,以為對方在說異男、異男的什麼碗糕洨。
幹,我們這群性別盲。
想一想,我是個在生活上相當笨拙的人,常以土法煉鋼的方式過著生活。這樣的人還奢望於物質層面上好好地照顧人,下場就是會惹出許多愚蠢的事蹟。我想好好地照顧人啊,我想拋棄愚蠢的技藝,彷彿我不曾出師一樣。
每日睡前都會焦慮地如廁,深怕尿床。請保佑下鋪的男子吧,萬天神佛。
/
同梯役男讀到我電腦螢幕上,PennySaf Chiang寫:「我們辦公室的異男又在跟另一個單位的女同事聊天」,興奮地問我,可愛的佩妮(我的同梯想跟佩妮要電話)所在的工作單位也有役男嗎?
這是倒反的程序。就跟胖胖對我說,他到現在聽到別人說「役男」時,也還是無法回神,以為對方在說異男、異男的什麼碗糕洨。
幹,我們這群性別盲。
Tuesday, January 27, 2015
浮雲:27 janvier 2015
趙姐埋怨雨日的計程車特別難招。險些趕不上八點的打卡。
趙姐將屆退休,是在消防局本部服務相當久的員工,憑著在此的年資幾乎熟記本部上下所有員工的臉與分機號碼;我在一樓服務台凡遇麻煩則都交由她處理。大許是女兒不生孩子的關係,趙姐多少有點,若有孫子,也都是我們這些替代役男孩的年齡的意思,所以把我們當孫子看。因此天天餵食役男,彷彿人一身有四個胃,不為反芻,只為餓。有趙姐,就不怕待在消防局的這年是饑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秘書室一樓的工友,順哥。
曉得我讀哲學,便丟石探路問我對宗教的興趣;曉得我讀過佛經,就正中下懷地聊起他的修行。我僅明白些許佛學概念,不過對順哥而言,光奢望在日常生活中能得一位稍懂佛學輪廓的人暢談已屬難得,每逢閒暇便湊在我身邊勸我修行。
有點為難啊,完全不想週五下班跟著到永和念經,也拒絕對佛經作任何本質論式的詮釋。順哥人好,但我壞,不受渡,餓鬼餓,貪玩人間,離我遠點。
趙姐將屆退休,是在消防局本部服務相當久的員工,憑著在此的年資幾乎熟記本部上下所有員工的臉與分機號碼;我在一樓服務台凡遇麻煩則都交由她處理。大許是女兒不生孩子的關係,趙姐多少有點,若有孫子,也都是我們這些替代役男孩的年齡的意思,所以把我們當孫子看。因此天天餵食役男,彷彿人一身有四個胃,不為反芻,只為餓。有趙姐,就不怕待在消防局的這年是饑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秘書室一樓的工友,順哥。
曉得我讀哲學,便丟石探路問我對宗教的興趣;曉得我讀過佛經,就正中下懷地聊起他的修行。我僅明白些許佛學概念,不過對順哥而言,光奢望在日常生活中能得一位稍懂佛學輪廓的人暢談已屬難得,每逢閒暇便湊在我身邊勸我修行。
有點為難啊,完全不想週五下班跟著到永和念經,也拒絕對佛經作任何本質論式的詮釋。順哥人好,但我壞,不受渡,餓鬼餓,貪玩人間,離我遠點。
Monday, January 26, 2015
浮雲:26 janvier 2015
下班前台北天空下起了雨。這似乎是我這個冬天,在這座城裡碰到的第一場雨。
仍然栽在消防局本部的一樓服務台鎮日。接了一通電話,劈頭問我幾點下班,糾正他,您指的是消防局員工的一般下班時間嗎?點頭稱是。以為我於此坐鎮一周,已然有了死拖客(stalker)的愛慕,結果是他人不擅的言詞,自己空然的虛妄。
禮拜一的工作日,強顏歡笑,與人為善。創世第一天的上帝應該也有很大的起床氣吧,就像盤古開天拿著斧頭要演什麼B級片一樣。
忽有幾朵桃花開來,湊近了,也不是我真的有興趣的對象。真正有興趣的對象,反而憂愁究竟是不是顆健康的蕊。每日有每日的思念,每刻也有每刻的歡興與憂愁;日日有日日的瘋魔,時時也有時時的捨念與執著。啊,雖貪玩人間,有時也會想,殺了我算了。
仍然栽在消防局本部的一樓服務台鎮日。接了一通電話,劈頭問我幾點下班,糾正他,您指的是消防局員工的一般下班時間嗎?點頭稱是。以為我於此坐鎮一周,已然有了死拖客(stalker)的愛慕,結果是他人不擅的言詞,自己空然的虛妄。
禮拜一的工作日,強顏歡笑,與人為善。創世第一天的上帝應該也有很大的起床氣吧,就像盤古開天拿著斧頭要演什麼B級片一樣。
忽有幾朵桃花開來,湊近了,也不是我真的有興趣的對象。真正有興趣的對象,反而憂愁究竟是不是顆健康的蕊。每日有每日的思念,每刻也有每刻的歡興與憂愁;日日有日日的瘋魔,時時也有時時的捨念與執著。啊,雖貪玩人間,有時也會想,殺了我算了。
浮雲:25 janvier 2015
我很少感到寂寞,然而自從入成功嶺、下台北市消防局專訓、而至秘書室內工作,都為了與各類人交際而感到焦慮。我是個在初識時不隨意透露心事的人,僅掏出耳朵默默觀察社群內部的運作規則,再選擇是否要親近或作個疏離的旁觀者。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都無法真心地融入成功嶺、專訓,甚至是秘書室的社群當中。也因為如此,我在這些環境中常顯得緊繃,得扮演某種並不真實角色與人說話,時間久了,就只想擁有獨處的時間,想休息,想去散步,也就感到寂寞。
我愛的人啊,寄望每個週末能與他們相見。回宿舍前夕難免感到心慌,又是一週。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東京物語》裡說,這座城這麼大,一不注意,人心就會在這裡走失。那麼就寄望所有週末,再尋回我、我們、你們。
我愛的人啊,寄望每個週末能與他們相見。回宿舍前夕難免感到心慌,又是一週。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東京物語》裡說,這座城這麼大,一不注意,人心就會在這裡走失。那麼就寄望所有週末,再尋回我、我們、你們。
浮雲:24 janvier 2015
我有些朋友不願安裝同志交友軟體,怕的是在生活圈內毫無預警地為人所出櫃。社會於今看似開放地接納同志,實則不然,對於同志的不友善很有可能只是更細微地藏入生活人事的紋理,而同志也就在這種狀況下,承受著更難以向外人所述的壓力與困境。
人是否決定自主地出櫃,對於當事者來說很可能有著更為實際的風險考量。比如說,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資源來對抗這些難以預料的、秋毫而難察的壓力。我比較不要臉,所以對於被出櫃後,可能面臨的險境,很少感到懼怕。然這不代表所有人都已備好自身,去接受櫃外紛然的友善與不友善。
我以為這是老生常談,但我所重視的朋友還是在他鄉碰到了這檔狗屁倒灶的鳥事,所以就再提了一次。相當憤怒。
幹。
這是敬人的穢語,也是穢人的敬語。不指名道姓,也就不幫你挪抬。
人是否決定自主地出櫃,對於當事者來說很可能有著更為實際的風險考量。比如說,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資源來對抗這些難以預料的、秋毫而難察的壓力。我比較不要臉,所以對於被出櫃後,可能面臨的險境,很少感到懼怕。然這不代表所有人都已備好自身,去接受櫃外紛然的友善與不友善。
我以為這是老生常談,但我所重視的朋友還是在他鄉碰到了這檔狗屁倒灶的鳥事,所以就再提了一次。相當憤怒。
幹。
這是敬人的穢語,也是穢人的敬語。不指名道姓,也就不幫你挪抬。
Friday, January 23, 2015
浮雲:9 janvier 2015
一、我獲得了相當好看的小說,所以進入內湖宿舍後,這週凡空閒我就讀小說。熄燈後只好就著窗外仍然輝煌的霓虹燈朦朧地讀。當大家為了緊急救護而用功讀著講義時,我在讀小說;當大家費神練習繩結時,我在讀小說。小說攝人心神,在那個法西斯主義盛行而沒人檢討的環境底下尤是。
二、當大家像拴緊的橡皮筋在唸書時,我就想抵抗。這種心境令我想起高三瘦懨懨的日子。
三、終日讀小說,緊急急救員的證照學、術科考試,最終竟拿了全班最高分。人生裡有多種「竟爾」的敘事轉折,就屬這種最爽。
四、好想散步。每天看著窗外的車流都在想「要是能舒適而放鬆地散步就好了」。
五、我多恨法西斯主義啊。以為離開了成功嶺的那個污染源,來到內湖還是躲不掉人生的劫數。學員長(簡單來說就像是小學生選出來的班長)竟僭越地點了兩名集合時遲到的學員到台前向大家道歉,只因為他為了大家好。
人這一輩子到底會被「為了大家好」這種話矇騙幾次呢?人要被矇騙幾次才會曉得我們究竟活在一個不尊重個體的社會裡呢?
二、當大家像拴緊的橡皮筋在唸書時,我就想抵抗。這種心境令我想起高三瘦懨懨的日子。
三、終日讀小說,緊急急救員的證照學、術科考試,最終竟拿了全班最高分。人生裡有多種「竟爾」的敘事轉折,就屬這種最爽。
四、好想散步。每天看著窗外的車流都在想「要是能舒適而放鬆地散步就好了」。
五、我多恨法西斯主義啊。以為離開了成功嶺的那個污染源,來到內湖還是躲不掉人生的劫數。學員長(簡單來說就像是小學生選出來的班長)竟僭越地點了兩名集合時遲到的學員到台前向大家道歉,只因為他為了大家好。
人這一輩子到底會被「為了大家好」這種話矇騙幾次呢?人要被矇騙幾次才會曉得我們究竟活在一個不尊重個體的社會裡呢?
夢:9 janvier 2015
這週在內湖宿舍做了兩則夢;兩則夢都令翌日清醒的人消沉。一則夢事關重要的人自此斷了聯絡;一則夢如昔,我夢到吳宥賢未死之時,多想告訴他不要死,我在這裡,我還在這裡。
我對人間仳離多有恐懼,也才汲汲營營學著與所有人告別。
我的表妹們年幼,成長的過程中都曾經歷過一個階段,拒絕與人告別。玩得夠開心的話,凡與人告別就撇嘴;真要走,人偌大的眼淚就一顆一顆掉下來。我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不能再用這種耍賴的方式要求任何遠行的人為我停下腳步。運命不為耍賴而心軟;軟到出血的永遠是人撲通撲通跳動的心。
聚時歡愉,散時難保瀟灑,但願好日西行。
我對人間仳離多有恐懼,也才汲汲營營學著與所有人告別。
我的表妹們年幼,成長的過程中都曾經歷過一個階段,拒絕與人告別。玩得夠開心的話,凡與人告別就撇嘴;真要走,人偌大的眼淚就一顆一顆掉下來。我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不能再用這種耍賴的方式要求任何遠行的人為我停下腳步。運命不為耍賴而心軟;軟到出血的永遠是人撲通撲通跳動的心。
聚時歡愉,散時難保瀟灑,但願好日西行。
浮雲:2 janvier 2015
所有不可預期的偶然都是禮物,雖則難保它必然是一種祝福。但願每次開啟禮物的當下我都能保有愛的能力,保有對世界的寬心與信任。願我開啟時,你是禮物,而我是祝福。這就是我今年對自己的期許。
浮雲:27 décembre 2014
一、寫論文最期待的是誌謝,毫不羞赧。──只是人呆滯,事蹉跎,論文的羊水不破,誌謝的手腳不現。但說不管,就不管。能穩健地活到現在絕非仰賴個體孤獨的手工業。那麼多人的絲線織就我無芯的蕊,沒人可以純然地稱我,也就敷著這軀毫無人稱的雜種存有活著。人因不純粹而有蓬勃的氣力,我對此總有謝意。
二、去年九月遷至南勢角有Nail Wu、Chipson Vincent、Roshan Vincent的幫忙。在往後的幾個月裡,大家一起在南勢角的那間房子裡吃飯、喝酒,用投影機看世足,Kaiping Hu一度要把褲子拖給菲看,PennySaf Chiang在那裡讓我首次瞭解女性乳房的觸感。荒廢的時光令人緬懷。
退房時我也來不及向樓下的麵攤老闆告別。
三、曼谷回來後,我始終都有分手在即的預感。你要出國,我要服役,人沒辦法踏在已知的岸上預測遠方的浪濤。所有的關係都必須站在自由的基礎上你才能明白地感受到愛及其矛盾、排他性及其包容。我們最終還是分手了,且一如我所寫的,「我們」分手了,那是兩個人一起處理的最後的功課,而且我們處理得很好。分手後我還是希望你快樂,希望你明白你曾被愛過,要因此感到自信,要因此明白自己的堅強,夜裡還是可以因為生活輾來的壓力而落淚,那都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因為你值得被愛。
四、柏是在後來搬到南勢角的附近,也沒想過這些巧合。人靠得近時不一定認識,認識有著四方歧路而來的成因。──那是揉成細緻芯蕊的繁稠絲線,看似幽幽,也像針縫,打那麼小一個結就可以刺繡。
五、我在成功嶺遺漏了所有於那時期寄來的簡訊。沒有一封抵達到我的手上。後來啞才補寄給我一封。我對啞說的話,也是我想對每一個我所提到而我重視的人說的話:我希望你們快樂。
幾年前我對陳奕傑說過:我無償給予的時候儘管拿,未來難保終有時:我給而你不願拿;我不給而你奢望拿;或我不給、你不取,世界太平。關係有它起始的意外,也有它令人措手不及的毀壞。希望我在時你們愉快;也希望有朝一日竟因為你們愉快,而我不在。
六、我記得你們每一個人的臉。
七、以為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不過短短一年。弱水三千里遠,也只是,一瓢水的事。
八、寤醒後很想讀書,想離開成功嶺的節奏回到自己習慣的星軌,拿筆寫字都好,就不想聽人拾起滿地說過的蠢話再說一次。在那裡簡直度過了一段人人都背起小吃店慣常張貼之格言的日子。不要懷疑,彼處人的基本邏輯是莫追問壓迫的結構,調整心念,世界隨著你的態度幻化,日子就能過得很好。我的心、我的腦,在那裡,怎麼沒有骨折呢?
二、去年九月遷至南勢角有Nail Wu、Chipson Vincent、Roshan Vincent的幫忙。在往後的幾個月裡,大家一起在南勢角的那間房子裡吃飯、喝酒,用投影機看世足,Kaiping Hu一度要把褲子拖給菲看,PennySaf Chiang在那裡讓我首次瞭解女性乳房的觸感。荒廢的時光令人緬懷。
退房時我也來不及向樓下的麵攤老闆告別。
三、曼谷回來後,我始終都有分手在即的預感。你要出國,我要服役,人沒辦法踏在已知的岸上預測遠方的浪濤。所有的關係都必須站在自由的基礎上你才能明白地感受到愛及其矛盾、排他性及其包容。我們最終還是分手了,且一如我所寫的,「我們」分手了,那是兩個人一起處理的最後的功課,而且我們處理得很好。分手後我還是希望你快樂,希望你明白你曾被愛過,要因此感到自信,要因此明白自己的堅強,夜裡還是可以因為生活輾來的壓力而落淚,那都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因為你值得被愛。
四、柏是在後來搬到南勢角的附近,也沒想過這些巧合。人靠得近時不一定認識,認識有著四方歧路而來的成因。──那是揉成細緻芯蕊的繁稠絲線,看似幽幽,也像針縫,打那麼小一個結就可以刺繡。
五、我在成功嶺遺漏了所有於那時期寄來的簡訊。沒有一封抵達到我的手上。後來啞才補寄給我一封。我對啞說的話,也是我想對每一個我所提到而我重視的人說的話:我希望你們快樂。
幾年前我對陳奕傑說過:我無償給予的時候儘管拿,未來難保終有時:我給而你不願拿;我不給而你奢望拿;或我不給、你不取,世界太平。關係有它起始的意外,也有它令人措手不及的毀壞。希望我在時你們愉快;也希望有朝一日竟因為你們愉快,而我不在。
六、我記得你們每一個人的臉。
七、以為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不過短短一年。弱水三千里遠,也只是,一瓢水的事。
八、寤醒後很想讀書,想離開成功嶺的節奏回到自己習慣的星軌,拿筆寫字都好,就不想聽人拾起滿地說過的蠢話再說一次。在那裡簡直度過了一段人人都背起小吃店慣常張貼之格言的日子。不要懷疑,彼處人的基本邏輯是莫追問壓迫的結構,調整心念,世界隨著你的態度幻化,日子就能過得很好。我的心、我的腦,在那裡,怎麼沒有骨折呢?
浮雲:26 décembre 2014
一、成功嶺替代役男的規訓方式就是養一群困獸要你們打開審查機制的條碼機刷刷對方、刷刷自己。很多時候我都不忍看隔壁替代役幹部訓練班的學員一眼,很多時候我都在生氣,──我不忍,但我沒轍,我就唱歌。
二、這梯沒什麼好選,最後拿了台北市消防局的缺。下週一,台北內湖專訓三週。
三、朋友要我好好參加替代役基礎訓練的心得競賽。就像對著泰迪熊軟布偶撒嬌那樣好好寫一篇文章。我的軟布偶是傅柯,也就對著傅柯撒嬌那樣好好地罵了這裡一頓。──寫得很好啊。可是沒得獎。
四、擔任總洗委的緣故,分隊長待我不薄,偷偷躲在會議室裡吃了麵包、喝了飲料。插別人的隊洗澡,大家見到我就說辛苦了。大許因為這樣拿到榮譽假比別人早些離開成功嶺。
五、謝謝各位對我的照顧。謝謝張展耀老是錯戴我的名牌、套我的鞋子、穿我的衣服。
六、衛福部的人談及愛滋令人不忍卒睹。
七、軍人啊、軍人,你怎麼可以蠢到要求所有因病重而咳嗽的役男在長官說話的時候不准咳嗽呢?
二、這梯沒什麼好選,最後拿了台北市消防局的缺。下週一,台北內湖專訓三週。
三、朋友要我好好參加替代役基礎訓練的心得競賽。就像對著泰迪熊軟布偶撒嬌那樣好好寫一篇文章。我的軟布偶是傅柯,也就對著傅柯撒嬌那樣好好地罵了這裡一頓。──寫得很好啊。可是沒得獎。
四、擔任總洗委的緣故,分隊長待我不薄,偷偷躲在會議室裡吃了麵包、喝了飲料。插別人的隊洗澡,大家見到我就說辛苦了。大許因為這樣拿到榮譽假比別人早些離開成功嶺。
五、謝謝各位對我的照顧。謝謝張展耀老是錯戴我的名牌、套我的鞋子、穿我的衣服。
六、衛福部的人談及愛滋令人不忍卒睹。
七、軍人啊、軍人,你怎麼可以蠢到要求所有因病重而咳嗽的役男在長官說話的時候不准咳嗽呢?
浮雲:7 décembre 2014
一、與F、其男友、幾年前來台灣旅行的德國友人一起晚餐。完全沒想過會再與該德國友人碰面。狹路相逢的意思是世界這麼大、路這麼寬,你偏偏這時來、我這時去。你偏偏來,偏偏來,命運的誕生也不過歪打正著。
二、沒想到這麼捨不得,雖然仍可能可以順利抽到在台北的單位,但一想到也很可能會有好一陣子沒辦法見到這些好友的笑容與憂愁,就覺得捨不得。
人有諸般不捨,我不捨的總是治絲益棼的人情。我困於人情,我再三為此受苦。──幸而如此,我總能看見人與人間珍貴而互相看顧的情份。
二、沒想到這麼捨不得,雖然仍可能可以順利抽到在台北的單位,但一想到也很可能會有好一陣子沒辦法見到這些好友的笑容與憂愁,就覺得捨不得。
人有諸般不捨,我不捨的總是治絲益棼的人情。我困於人情,我再三為此受苦。──幸而如此,我總能看見人與人間珍貴而互相看顧的情份。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