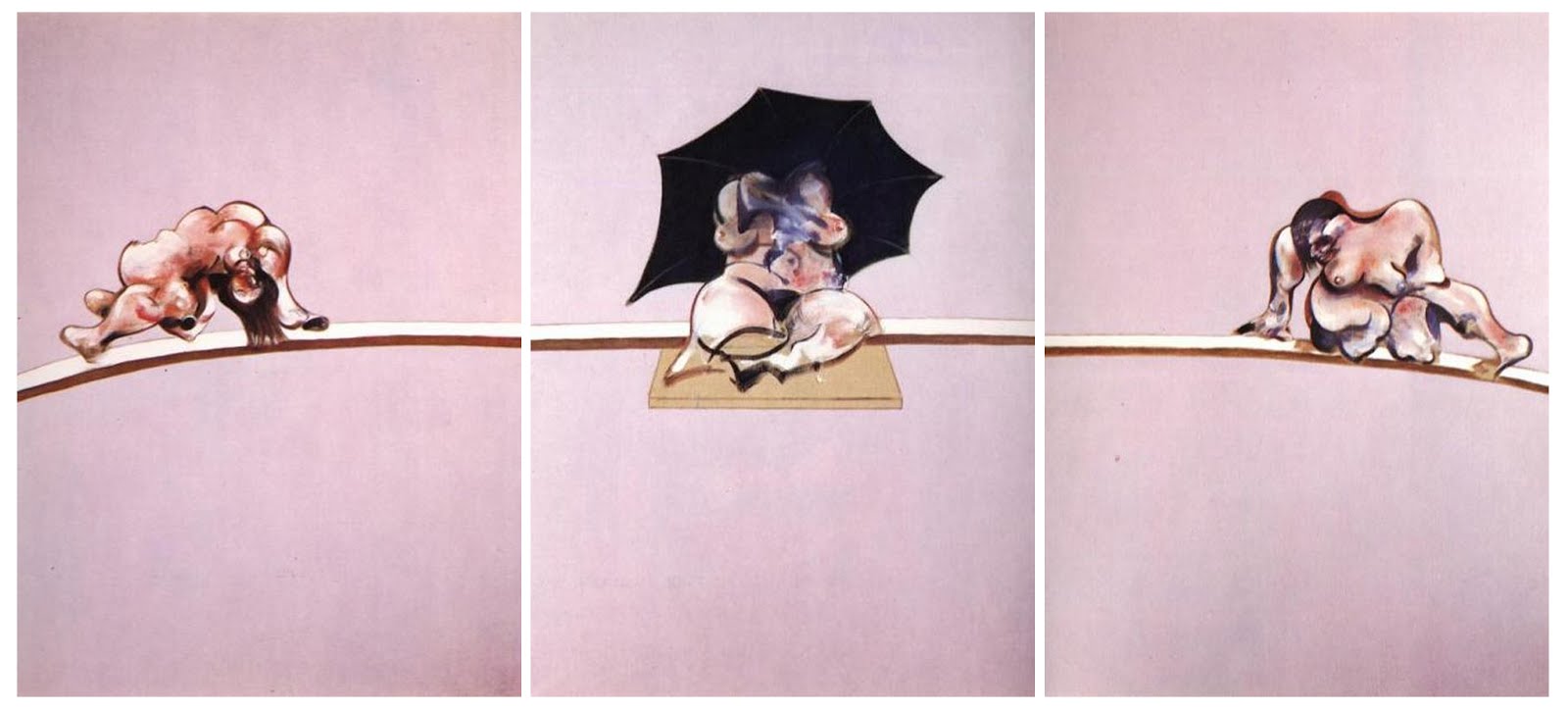讀研究所時,Ch有一陣子很是焦慮,我們會在政大的麥側點菸,他聊起自己多少歲數的人了還執迷不悟地讀一門不可能養活自己的學科,但現在是誰在巴黎為了這門學科泡珍珠奶茶努力地掙生活呢?
他的焦慮每隔一陣子就會出現,冤親債主來索命一樣沒在跟你罷休的。也因此我們每隔一陣子就會開啟déja vu一樣的對話,應答與談吐都是排練,也是現場演出。若是演唱會,我們是原地巡迴。有好幾次他都若有意識地問:「你會不會覺得我很煩,每次都聊同樣的事。」
我可能招誰惹誰,朋友若有關係裡的困難、走不過去的情關,大劫臨頭想擋煞,有時就會想起我。我石敢當。
在傾聽的過程有時延續幾日、偶爾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都會聽到對方同你訴說著一樣的事,應該在上次的談話裡,我們便已說過的話題,而也一起想出對策了,怎麼如今人還是像在四百公尺的操場上奔跑,彷彿在前進的路途裡卻什麼地方都到不了,人執迷不悟,想成佛卻不得一偈。
──我很常想起Ch當時歉疚的臉問我,你會不會覺得我很煩,每次都聊同樣的事。
在焦慮裡,孔雀東南飛,五步一徘徊,誰不是這樣,誰生來是Siri。畢竟我們處理的是情感,不是理智、不是計算。
我在Ch的經驗裡明白的事情是,在等待造成焦慮的困境有所解答的過程裡,會有許多脆弱的時刻。在人忽然化為小心輕放、內有易碎品之身的時刻,你就會起了疑惑,然後對你信得過的人發問,問一樣的問題。
每一次他都需要一個相同的解答,告訴他,給他肯定,說你非隻身一人,你為人所理解。
或者就算無法理解,我的男友也會告訴你,就算我不能明白,不能水落石出,在那麼湍急而視線無法穿越的河水之中,我都在,沉沉地是一粒石頭,在你旁邊。
Friday, June 23, 2017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