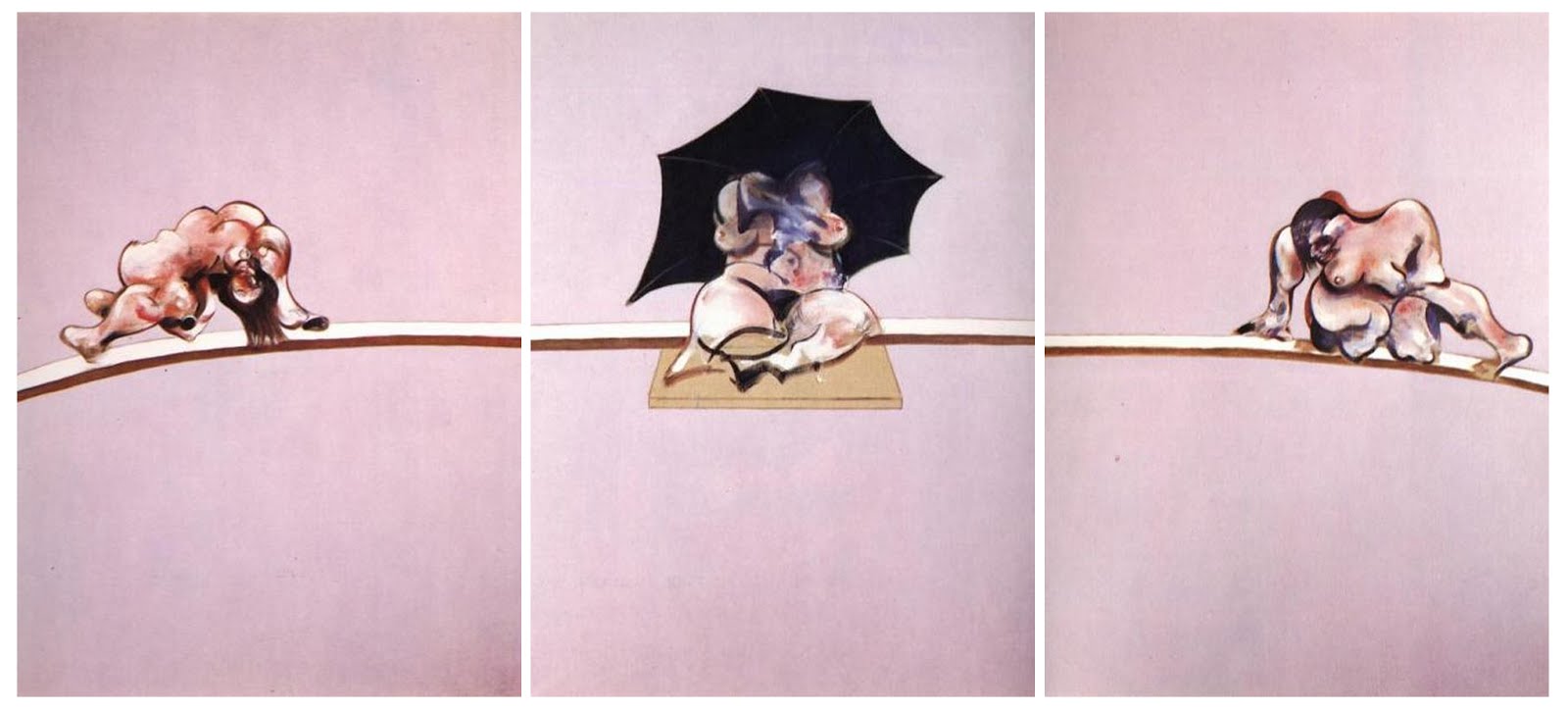連日失眠,雖然皆可睡至正午,然夜裡寂然百無聊賴,隔日亦因感冒而備感昏沉;加上每天都有被文本追著跑的焦慮,我總有無暇兼顧他者的念頭,甚至無心聽完別人說完一件生活的細瑣。
昨天仍然睡不著。無所為就在網路上看鬼故事──即便相信最穩實可靠的莫是我所倚的世界,所有苦痛、憂懼、愛恨、慚愧都在這裡,卻也還是害怕,如童騃時,為看不見而仍能左右你人生的事物所驚疑。從前是鬼魅,如今則以其他形式出現,如摯友在你看不見的背面自殺,如隔日忽聞男友說「不愛了」,如夢裡驚覺青春魄散、身衰體竭,這麼老,彷彿不曾年輕過,遂痛哭枕被。
彷彿從幼樨至此不曾長大過;面對這個世界的慮患猶深。始終意識到自己的身後有枚氣孔,而你永遠無法將之扣上,便讓自己洩氣乾癟,癱軟,而終跪伏於地。
/
生之難,也就忽爾覺得,生之堅硬,令人敬佩。
Thursday, November 24, 2011
Tuesday, November 22, 2011
Nov.21st
媒體是你更大的身體。
/
幾日熬夜、喝酒、吃菸,今午寤醒吞嚥口水覺得痛。在終於感到冬日腳步臨近的下午成了餓鬼,物過喉頭而墜成一團火焰。沖過澡下山看醫生。忘了攜帶今日到期的光碟,遂折返回寢室再迢迢下山晚餐;吃清淡的麵湯,覆以臉容大的芙蓉蛋花。晚些栽於圖書館讀德希達《導論》,總怪罪自己愚魯,然興許讀書而能束己膽魄續而前行的關鍵並不在於此人聰明與否,而在於毅力與誠心。我不免害怕自己常是容易放棄的人。
開始讀董啟章《啞瓷》。幾年前開卷讀過,未竟;年初趁閒暇將《栩栩》讀完,希望能接續著讀,在年終前讀完。
/
幾日熬夜、喝酒、吃菸,今午寤醒吞嚥口水覺得痛。在終於感到冬日腳步臨近的下午成了餓鬼,物過喉頭而墜成一團火焰。沖過澡下山看醫生。忘了攜帶今日到期的光碟,遂折返回寢室再迢迢下山晚餐;吃清淡的麵湯,覆以臉容大的芙蓉蛋花。晚些栽於圖書館讀德希達《導論》,總怪罪自己愚魯,然興許讀書而能束己膽魄續而前行的關鍵並不在於此人聰明與否,而在於毅力與誠心。我不免害怕自己常是容易放棄的人。
開始讀董啟章《啞瓷》。幾年前開卷讀過,未竟;年初趁閒暇將《栩栩》讀完,希望能接續著讀,在年終前讀完。
Monday, November 7, 2011
集郵
薄霧掩至的夜裡,他開著車來,在小公寓潔白無邪的床單上與她做愛,睡至天明,然後在中午前離開,為他的現任女友接機。
他離開的時候萬里晴空飄著幾朵烏雲,而她始終不明白為何氣象報導可以肯定地說出:「今天將會是個大晴天。」到底要有幾片烏雲的鳩集才不算晴天?或者說,陰天少掉幾片烏雲後才算天晴呢?有沒有可能,天氣與親密關係總是愛與不愛的混雜、流動;對於一個人,你既愛,也不愛;那麼,「我們是男女朋友」到底是甚麼意思呢?要愛多少,我們才能算是一對戀人?或是不愛多少,我們就不是一對戀人了?
她不知道。
下次他來的時候,寒流恰至,夜裡她倆圍著毛毯看電影,四隻腳丫相互交疊;她問:「這次女友工作幾天?」「幾天吧。」他的女友是個空姐,每個月輪番出境,他便開著小車來與她過夜;冬夜的路上排煙管熱呼呼地呵氣,她總關切他來時的天氣,叮囑天冷,天熱;天晴,天雨;行路安全。
她是他的秘書,見過她女友幾次。那麼漂亮的一個女孩子,學歷高,英、法語溜得不得了;進辦公室時,她請她稍待,經理開完會便來;她含秀點頭,大家閨秀的模樣,彷彿粗暴對待,花苞皆落。她望著她婀娜身影坐在那,不忍自卑起來;可同時想像她與他到底會如何做愛呢?會魯莽地叫她跪下含他嗎?當他從背後上來時,她會哀求自己還要嗎?她會主動跨在他的身上,逐漸找到韻律地搖起身子來嗎?她願意讓自己多淫蕩,讓這個世界可以看到多少變化多端且流動不滯的臉容呢?
看電影的那個晚上,她問起他這些問題;男人望著天花板想了一下,緩緩說:「不會。我們相敬如賓。相敬如賓是我們愛的方式。」她低頭揣想,那麼狂野淫蕩,便是她與他另外一種愛的方式;正因如此,她漸漸不感到自卑了。如果她的愛讓他展現了節制與尊重,那麼她的愛遂恰恰相反,在她的背面開啟了他的另外一個面容。
她於焉得到一枚,她從沒得到過的面容。一個世界。
他離開的時候萬里晴空飄著幾朵烏雲,而她始終不明白為何氣象報導可以肯定地說出:「今天將會是個大晴天。」到底要有幾片烏雲的鳩集才不算晴天?或者說,陰天少掉幾片烏雲後才算天晴呢?有沒有可能,天氣與親密關係總是愛與不愛的混雜、流動;對於一個人,你既愛,也不愛;那麼,「我們是男女朋友」到底是甚麼意思呢?要愛多少,我們才能算是一對戀人?或是不愛多少,我們就不是一對戀人了?
她不知道。
下次他來的時候,寒流恰至,夜裡她倆圍著毛毯看電影,四隻腳丫相互交疊;她問:「這次女友工作幾天?」「幾天吧。」他的女友是個空姐,每個月輪番出境,他便開著小車來與她過夜;冬夜的路上排煙管熱呼呼地呵氣,她總關切他來時的天氣,叮囑天冷,天熱;天晴,天雨;行路安全。
她是他的秘書,見過她女友幾次。那麼漂亮的一個女孩子,學歷高,英、法語溜得不得了;進辦公室時,她請她稍待,經理開完會便來;她含秀點頭,大家閨秀的模樣,彷彿粗暴對待,花苞皆落。她望著她婀娜身影坐在那,不忍自卑起來;可同時想像她與他到底會如何做愛呢?會魯莽地叫她跪下含他嗎?當他從背後上來時,她會哀求自己還要嗎?她會主動跨在他的身上,逐漸找到韻律地搖起身子來嗎?她願意讓自己多淫蕩,讓這個世界可以看到多少變化多端且流動不滯的臉容呢?
看電影的那個晚上,她問起他這些問題;男人望著天花板想了一下,緩緩說:「不會。我們相敬如賓。相敬如賓是我們愛的方式。」她低頭揣想,那麼狂野淫蕩,便是她與他另外一種愛的方式;正因如此,她漸漸不感到自卑了。如果她的愛讓他展現了節制與尊重,那麼她的愛遂恰恰相反,在她的背面開啟了他的另外一個面容。
她於焉得到一枚,她從沒得到過的面容。一個世界。
變形記
計程車沿著海行駛,F與我在後座聊著、搭著。陽光赤焰,日暮時分仍然曬得海面燃燒,灼人。他說:「好奇怪,現在才有離開的感覺。」我看著他,而他繼續說:「好像當初還住在德國,台灣只是短暫的停留。」
我們甚有默契,並不說「回台灣」;移民第二代回哪裡呢?「回」作為一種歸復,我想不出F除了他自身,還有哪裡可以入籍。
他並沒有中心;他的中心是自己。而他自己這麼邊緣。薩伊德。
機場內我推著行李,F的母親與我談話;早先我在F與母親台北的居處同他整理著行李,說笑;因有共同的背景而顯得靈犀,同時,同地,喊出一樣的字句。我們活在隱喻與象徵的世界;他願意讓我進入那間母親(九月母親將前往德國工作)與他的臨時寓所,紙箱堆疊溢至天花板;空間那麼小,而生活可以這樣摺疊。偶爾我看著這些摺紙般的行囊感到疑惑,搬遷四處實際上是種減法的人生,總是與物對峙,丟棄,留著那些緊貼肌膚最近的物事,賸餘的皆是欲望。
直到你立地扎根,莖葉展脈,人才瞬間立體地茁壯;與城胼胝。甚至是帶有侵略性的滲入。
F聯絡新加坡的友人妥當。這些年來真實親近他的人散落於世界各處;Isa 人在西班牙、Nam 在德國、Rita在印尼、寶寶在馬來西亞,而台灣遂成為我。
我駐軍此處,保衛一些什麼。
離開前F主動踏前擁我,我有語無言;並非所有的情事均得以拿語言兌換,總有一些禮物換不出來。總有遊樂場的票券,綑成迷宮,藏在抽屜好幾年。
這次工作簽約就是兩年新加坡的日子;那瞬間我想起浦島太郎。那起合約如木盒魔煙,再見,我仍在政大研所,他則要簽拾另一種生活。
遠處雲塊漂移;生活無非位移,變形,偶爾日頭豔如煉獄,或者兩朵雲相遇哭成一團。我們書寫變形記。我們無常。
我們甚有默契,並不說「回台灣」;移民第二代回哪裡呢?「回」作為一種歸復,我想不出F除了他自身,還有哪裡可以入籍。
他並沒有中心;他的中心是自己。而他自己這麼邊緣。薩伊德。
機場內我推著行李,F的母親與我談話;早先我在F與母親台北的居處同他整理著行李,說笑;因有共同的背景而顯得靈犀,同時,同地,喊出一樣的字句。我們活在隱喻與象徵的世界;他願意讓我進入那間母親(九月母親將前往德國工作)與他的臨時寓所,紙箱堆疊溢至天花板;空間那麼小,而生活可以這樣摺疊。偶爾我看著這些摺紙般的行囊感到疑惑,搬遷四處實際上是種減法的人生,總是與物對峙,丟棄,留著那些緊貼肌膚最近的物事,賸餘的皆是欲望。
直到你立地扎根,莖葉展脈,人才瞬間立體地茁壯;與城胼胝。甚至是帶有侵略性的滲入。
F聯絡新加坡的友人妥當。這些年來真實親近他的人散落於世界各處;Isa 人在西班牙、Nam 在德國、Rita在印尼、寶寶在馬來西亞,而台灣遂成為我。
我駐軍此處,保衛一些什麼。
離開前F主動踏前擁我,我有語無言;並非所有的情事均得以拿語言兌換,總有一些禮物換不出來。總有遊樂場的票券,綑成迷宮,藏在抽屜好幾年。
這次工作簽約就是兩年新加坡的日子;那瞬間我想起浦島太郎。那起合約如木盒魔煙,再見,我仍在政大研所,他則要簽拾另一種生活。
遠處雲塊漂移;生活無非位移,變形,偶爾日頭豔如煉獄,或者兩朵雲相遇哭成一團。我們書寫變形記。我們無常。
種子與現行
電視播著奇異果的廣告,便洗了刀子、湯匙,將擱置幾天的奇異果切了。初購入的青奇異果放了幾天也還是硬的,酸的。小時候外婆不敢吃酸,便趁著我在的時候,將奇異果削皮,切片,擺盤,我吃得嘴裡澀澀的。國小的營養午餐也時常發放奇異果,我常將之置於書包底,幾天後若非水果兀自腐爛發出腥臭,便是書本把果皮都壓碎了,沾了書頁都是髒的;即便拿吹風機,攤平於陽光底下,那味道都如銘印般烙上去了,久久不散──佛家裡的唯識學派遂取之意象而成薰習,以古典制約反應來說明的話,即狗狗聽到鈴聲便流口水,那是因為鈴聲成為一種符號,反覆多次,薰習成一個種子,藏在狗的意識裡,此後若再聽到鈴聲,種子便會於意識中騰起「進食」的現行。
都說薰習,我第一次讀到這字時,想到的竟然是港式燒臘裡的燒鴨燒雞的,讓柴火與烤汁燒入皮肉裡。
奇異果固然成為一截符號,讓我吃食之際,總回想起外婆,又或是國小骯髒的書本與書包。幾年前寫過,這些符號也是很容易再遭到覆寫的──讓我記起初戀的歌曲若再多聽幾次,那記憶便會顯得比較薄弱,再多聽,則歌曲亦成為我記憶其他事情的鏈結。唯識裡談種子與現行的關係是互相影響的。種子有在意識裡騰起現行的潛能,現行,也就是意識,或是行為,則也有可能回頭改寫種子,而薰習成一個新的種子。故,種子現行如瀑流,從來都沒有間斷,互成因果。
因果呀因果,佛家若談因果遂無法不談空,空亦復空,人呀,無常。
奇異果仍能在超市裡買到,也還是酸,外婆呀,死了都不知道有幾年囉。
都說薰習,我第一次讀到這字時,想到的竟然是港式燒臘裡的燒鴨燒雞的,讓柴火與烤汁燒入皮肉裡。
奇異果固然成為一截符號,讓我吃食之際,總回想起外婆,又或是國小骯髒的書本與書包。幾年前寫過,這些符號也是很容易再遭到覆寫的──讓我記起初戀的歌曲若再多聽幾次,那記憶便會顯得比較薄弱,再多聽,則歌曲亦成為我記憶其他事情的鏈結。唯識裡談種子與現行的關係是互相影響的。種子有在意識裡騰起現行的潛能,現行,也就是意識,或是行為,則也有可能回頭改寫種子,而薰習成一個新的種子。故,種子現行如瀑流,從來都沒有間斷,互成因果。
因果呀因果,佛家若談因果遂無法不談空,空亦復空,人呀,無常。
奇異果仍能在超市裡買到,也還是酸,外婆呀,死了都不知道有幾年囉。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