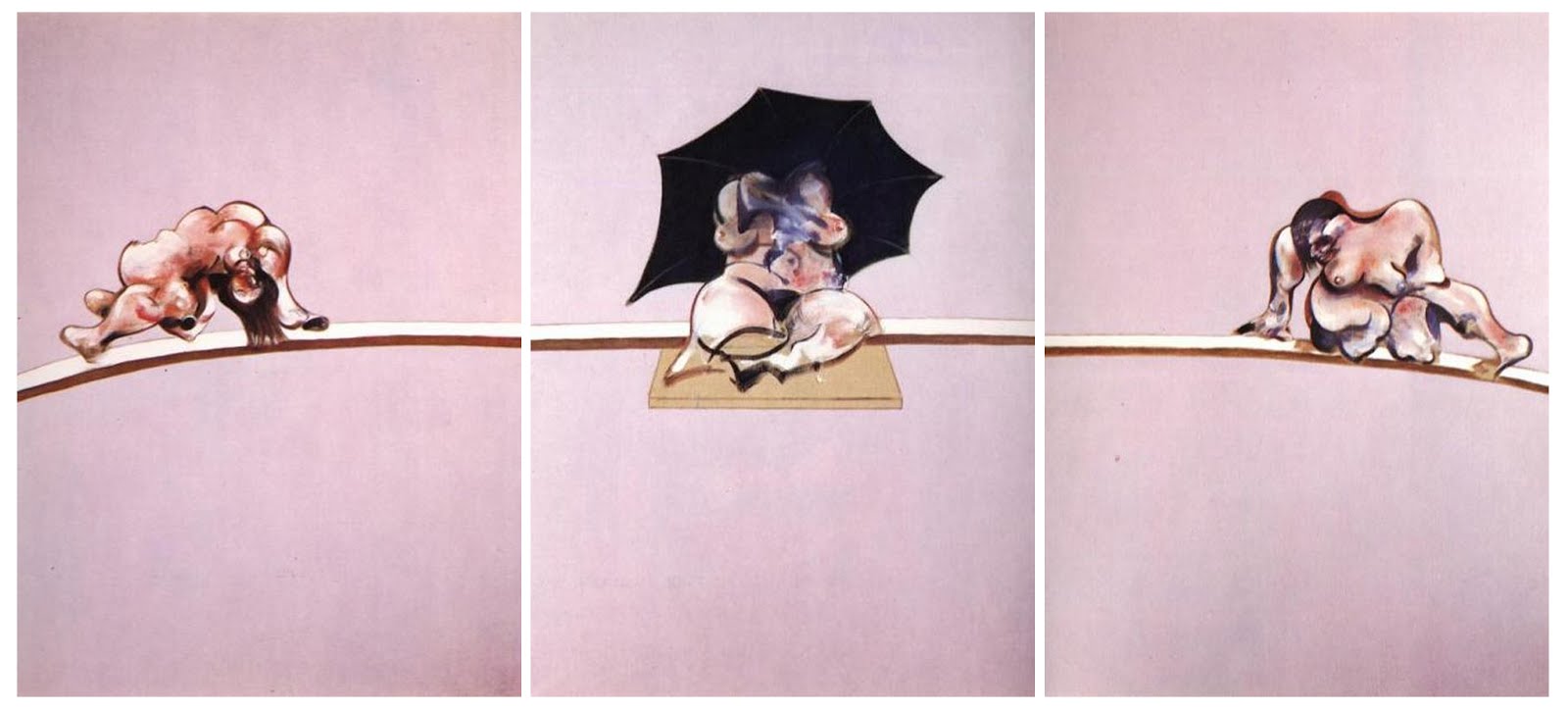待人唯誠。不誠無物。
非常感謝兩年來曾經共事的那些人。
有些人我討厭。有些人我喜歡。
雖然我們都知道在惡魔冰淇淋門市底下工作竟是這麼辛勞的事情。好比說當人潮如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那般拖泥帶水,而我們從早到晚工作十幾個小時仍需微笑。不巧這時冰淇淋竟然硬得春光明媚,每個人隔天彷彿都可以領著身障手冊灑著碎花繼續埋頭工作。我們明白販賣冰淇淋之艱難啊。以為收拾完客人的殘局,凌晨四點,門市的燈都關好了,倉庫的燈就亮了。老天爺,冰淇淋都賣完了不連夜趕製明天賣什麼?所以有人就把冰淇淋製造機搬到自己的住處,將衣櫃改造成巨大的冷凍冰箱,她說,我要回家。回到自己落寞的人生裡孤寂無語,她說,我留下來做冰淇淋。
她紅鸞星從沒動過。
雖然我們都知道,工作艱難。偶爾想起我亡故的友人,那些游離於生死寐醒之間的家人,你仍然必須說:請問有吃過我們的冰淇淋嗎?需要幫你介紹嗎?我這裡幫你製作冰淇淋。聽過我們唱歌嗎?那麼我們唱歌給你聽。你的冰淇淋好囉!前面幫你結帳。這樣總共是兩百三十元。需要搭配任何飲品一起享用嗎?好。小心拿。謝謝你。掰掰。
拿起鈴鼓,再唱一首歌。
雖然我們都知道,各自疲累,身體開始微小地崩壞。熬夜。精神不濟所引起的偏頭痛。痛了好些天還是回到原處握著挖冰勺與那些宛如冷凍的石頭之冰淇淋搏鬥,同它們喊話:你以為硬起來我就會色慾薰心嗎?少來了。冰淇淋這麼硬,怪不得叫冷石頭。拿鏟挖石,有人挖得右手盡失知覺,不可動,不能動。有人拿鏟挖石,挖得笑臉盈盈暗自咒罵,幹。也有人超時站立,鶴立雞群,立得靜脈區張彷彿河圖。
雖然我們都知道。
對。我們都知道。
簽下惡魔契約販賣身體勞力與時間的那些總總艱難,然而非常感謝你們這兩年來願意體諒與分擔的善意。願意聽我說笑話,陪我玩耍,說許多小秘密給我聽。謝謝你們願意相信我,陪我吃消夜,與我增肥。這些願意都將成為善意,支撐生活,使之更有厚度。
這封信獻給這些人:法蘭克。林卡羅。鴨子。晃。賴肥拉。陳小歐。雞妮。瑞秋。貝蒂。莎娜。媞娜。兜呢。坎狄斯。帕克。休娜。亨瑞。艾力恩。顏秋瑤。張達西。洪恰克。馬菲斯。馬莉恩。盧哲群。查理斯。威力。凱特。摩妮卡。艾莉。蔓狄。喬安。伊芙。恰恰。丹尼斯。菲莉卡。徐偉倉。熊雪莉。林凱許。許黛比。凱倫。鴨米。矮愣。安妮。吳卡羅。憨瑞。傻妞。摳拉。克莉絲。李昌庭。
歡迎光臨。謝謝你。掰掰。
Saturday, February 11, 2012
Wednesday, February 8, 2012
劫為連理
昨天回台北,第一任感情複雜的不是男友密我,問我是不是有回高雄。言下之意是,我怎麼沒有找他出來。那是第一次在分開以後他主動以這種口氣嗔怪我。那年他因為交了女友,所以才知道我喜歡他,接著對我採取的措施就是疏離。我難過了好久,整個人像是當機那樣,僅僅維持著進食與哭與睡的人形。離開高中後,我從不敢明目張膽地找他,他也沒有聯絡過我。唯一一次見面是吳宥賢的告別式。
兩年前再碰到他時,我想問清楚當初他在想什麼呢。我的第二任不是男友是他的同班同學,我們的關係他看在眼底,亦曾對我說過,「你越是跟他親近,我越是不可能回來了。」我不明白,我甚至有點生氣,你都已遠離,憑什麼要我為你留白呢?卻又對他感到抱歉。高中的他鮮少跟人說心事,我大概是那兩年他可以安心託付同我說大小事的人,疏離如同斷臂;相信當他知道我對他的情愫時,傷害也逐漸形成了。
愛一個人竟然會感到抱歉。聽起來有多怪謬呢?
只是,我始終都有疑惑;縱使對他抱歉,我同時也對他負氣:你怎麼可以用這種疏離的方式對待我呢。噯,對他的情感複雜呀。
當年的人情災禍哭過幾個月熬是熬過去了,可劫難終成結呀,我想解開所以問過他,然他千篇一律的回答均是,「過去的事過去了就不用再提。」總之我們後來這一年來復得的相處大概就像是昨天聊天的模樣,溫馨得知對方的近況,不提過去的那件事,彷彿我們未來前途光明仍會繼續成為朋友。
我想起小時候吃桃子時覺得奇怪,桃子好好吃,可是咬到果核很痛很刺。桃子好可愛唷,可是果核好醜唷。我的意思是,有些傷害或者事件的核心就這樣被非常甜美漂亮的汁肉包覆。
那麼多年後,傷害變成我自己的事情了。
兩年前再碰到他時,我想問清楚當初他在想什麼呢。我的第二任不是男友是他的同班同學,我們的關係他看在眼底,亦曾對我說過,「你越是跟他親近,我越是不可能回來了。」我不明白,我甚至有點生氣,你都已遠離,憑什麼要我為你留白呢?卻又對他感到抱歉。高中的他鮮少跟人說心事,我大概是那兩年他可以安心託付同我說大小事的人,疏離如同斷臂;相信當他知道我對他的情愫時,傷害也逐漸形成了。
愛一個人竟然會感到抱歉。聽起來有多怪謬呢?
只是,我始終都有疑惑;縱使對他抱歉,我同時也對他負氣:你怎麼可以用這種疏離的方式對待我呢。噯,對他的情感複雜呀。
當年的人情災禍哭過幾個月熬是熬過去了,可劫難終成結呀,我想解開所以問過他,然他千篇一律的回答均是,「過去的事過去了就不用再提。」總之我們後來這一年來復得的相處大概就像是昨天聊天的模樣,溫馨得知對方的近況,不提過去的那件事,彷彿我們未來前途光明仍會繼續成為朋友。
我想起小時候吃桃子時覺得奇怪,桃子好好吃,可是咬到果核很痛很刺。桃子好可愛唷,可是果核好醜唷。我的意思是,有些傷害或者事件的核心就這樣被非常甜美漂亮的汁肉包覆。
那麼多年後,傷害變成我自己的事情了。
Tuesday, February 7, 2012
一瞬之光
午后閒散,找屋看屋租屋。我走著走著竟然想起以前的事。
生命中總有一些人猶如靈光一現,他們短促的在生命某段時期中出現,復又泯滅。曾經在錯落的航線中各自別過船頭,讓轉動的燈光掃過對方的顏面便又消失於遠方濃霧的景深之中。我想,阿光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阿光是個乾淨好看的女子,然而短髮俐落,球衣球褲的。離開重考班後好多次得回去辦考試事宜,每每回去她總撲來擁抱,整具軀體重量皆壓於我身,然後嘴裡嚷嚷你怎麼來了你怎麼來了。通常我刻薄酸她,她便笑。她笑起來很好看,臉白齒貝,雙頰於冬日還會微紅。不笑時眼睛澄明,一笑雙眼更如彎月,好像天空中,所有日之美好、夜之美好都在她臉上了。
阿光好相處,站在她身邊,我都不像男孩子。我坐在玄關看自己的書,她總要闊步前來翻過書面看書名,問我好看嗎,好看在哪,有時像麻雀。或者我瞇眼睨她,她便會不服氣喊,欸別看我這樣我也很文藝好不好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最後都在搞笑。都在搞笑的文學譬如一次國文作文,她寫不出來就寫一首諷刺國務機要費的打油詩。她甚自豪,押運押韻唸給我聽。
與阿光熟了,是在一次試後,同王筱筱一齊去書店及打電動。累時便坐下來聊天,聊瑣事。那次她向我坦承她喜歡的同是女子。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情事不過如此,身體有開有合,靈魂遂在其中來去悠遊,一切的記憶與遺忘都如同灌頂我們始知道,對方究竟是如何走過、如何生存,如何生命微小卻勇敢。然後交換靈魂,因而有了勇氣走出粟般一步。
後來的我離開了重考班,成了都市裡的無主孤魂,我們見面的次數也漸漸少了。放榜時知道她上了高雄大學的外文系,同一個從前同樣在重考班現今在高師大英語系唸書的女子交往。然後其音訊便如黑暗裡的一條細密蠶絲,斷了,不復尋了。偶爾我會想起這樣的一批人:他們的名姓在你生命中某一段時光裡如彩鱗般閃耀,而又當生命的聚光燈移位以後,他們的火光便逸散了。一瞬間的閃神我問我自己,現在的阿光究竟在幹麻呢?生命的航線各自畫開,哪裡有燈塔?哪裡又有風雨?我不知道,我僅僅是想起,然後復又走回現世,繼續找屋、看屋、租屋。
生命中總有一些人猶如靈光一現,他們短促的在生命某段時期中出現,復又泯滅。曾經在錯落的航線中各自別過船頭,讓轉動的燈光掃過對方的顏面便又消失於遠方濃霧的景深之中。我想,阿光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阿光是個乾淨好看的女子,然而短髮俐落,球衣球褲的。離開重考班後好多次得回去辦考試事宜,每每回去她總撲來擁抱,整具軀體重量皆壓於我身,然後嘴裡嚷嚷你怎麼來了你怎麼來了。通常我刻薄酸她,她便笑。她笑起來很好看,臉白齒貝,雙頰於冬日還會微紅。不笑時眼睛澄明,一笑雙眼更如彎月,好像天空中,所有日之美好、夜之美好都在她臉上了。
阿光好相處,站在她身邊,我都不像男孩子。我坐在玄關看自己的書,她總要闊步前來翻過書面看書名,問我好看嗎,好看在哪,有時像麻雀。或者我瞇眼睨她,她便會不服氣喊,欸別看我這樣我也很文藝好不好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最後都在搞笑。都在搞笑的文學譬如一次國文作文,她寫不出來就寫一首諷刺國務機要費的打油詩。她甚自豪,押運押韻唸給我聽。
與阿光熟了,是在一次試後,同王筱筱一齊去書店及打電動。累時便坐下來聊天,聊瑣事。那次她向我坦承她喜歡的同是女子。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情事不過如此,身體有開有合,靈魂遂在其中來去悠遊,一切的記憶與遺忘都如同灌頂我們始知道,對方究竟是如何走過、如何生存,如何生命微小卻勇敢。然後交換靈魂,因而有了勇氣走出粟般一步。
後來的我離開了重考班,成了都市裡的無主孤魂,我們見面的次數也漸漸少了。放榜時知道她上了高雄大學的外文系,同一個從前同樣在重考班現今在高師大英語系唸書的女子交往。然後其音訊便如黑暗裡的一條細密蠶絲,斷了,不復尋了。偶爾我會想起這樣的一批人:他們的名姓在你生命中某一段時光裡如彩鱗般閃耀,而又當生命的聚光燈移位以後,他們的火光便逸散了。一瞬間的閃神我問我自己,現在的阿光究竟在幹麻呢?生命的航線各自畫開,哪裡有燈塔?哪裡又有風雨?我不知道,我僅僅是想起,然後復又走回現世,繼續找屋、看屋、租屋。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