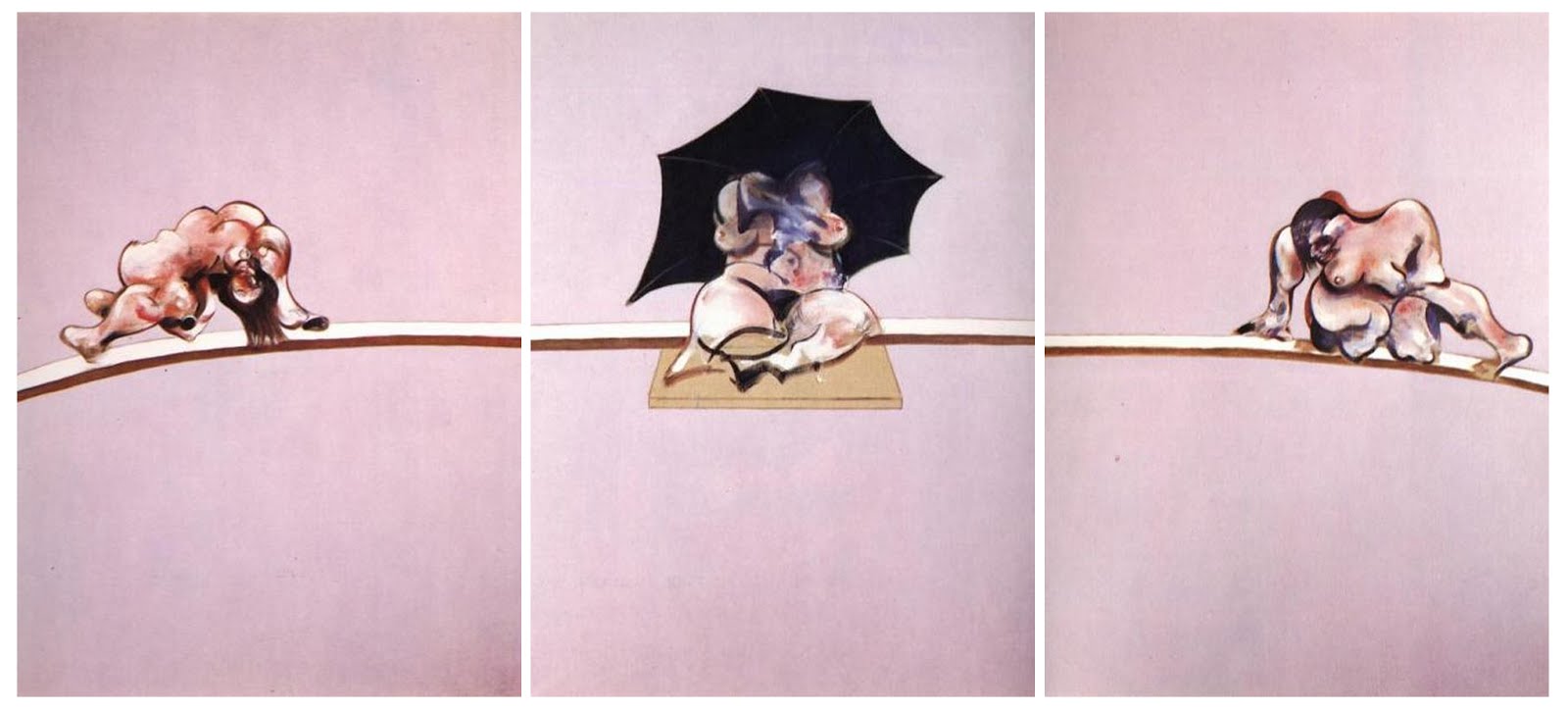我的母親在我居於臺北時,肯定常逡巡我的房底收拾雜物,抽屜裡其實有幾張我當初為了製作男友的生日卡片,而洗出來的,一起去泡湯屋、聽椎名演唱會,爬太平山所攝下的合照。
開開心心的,關於她的兒子及其男友的合照,毫不掩飾,或說是少跟腦筋地,就放在她可以抵達的觸目所在。
母親的態度當然比父親開放得多,她不太在意我過著什麼風格的人生,而不求大福富貴,只在意我是不是過得有尊嚴一點。
即,在意我繼承了什麼樣歷史所構造出來的身份,而有著專屬而獨特的當代經驗,男同志經驗,以及苦難。
她不會這麼假掰。上述那段話都是我自己的小劇場。
我只是疑惑,在我不在高雄的那段時間,她若進房,偶然觸及這些合照,心底究竟想些什麼。母親雖不干涉我的男同志身份,曉得這些事,也是這十年來的事了。她不是一般保守的女性,在那一輩人裡她許是很前衛的,然我不認為,她可以那麼輕易地揚棄兒子所帶來的某種震驚、不解,以及她自己對於世界所期待的秩序。
我的母親,到底曾/正歷經什麼樣的心路,且如同我一般,那很可能只有她一個人必須孤獨面對的呢?
Monday, April 16, 2018
Thursday, April 12, 2018
來亂的還是玩真的──專訪祈立峰(及其後記)
前陣子凱文捎了一份工作來,是聯合文學專訪最近出新書的祈立峰。雖然先前在公關公司沒實際做過人物專訪,但流程大致明白,就接下來。
過程都順利,惟落筆後發覺有些問題可以再問深一些,然而這就是訪問當下的敏銳度與技巧。有些材料是在落筆後才意識到,不夠多、不夠深,雖然這都可以經過修辭來掩飾,卻是騙不過自己的。未來也許還會接類似的工作,也許不會。然關於技能,還是不可不提醒自己。
* * *
撰寫:陳佑瑋
攝影:YJ
刊登網址:http://www.unitas.me/?p=2126
今年二月,祁立峰出版了他最新散文集《來亂》。書名承襲他一貫的惡趣,彷彿去年那個在茫茫文獻之中尋找我族身影的資深鄉民這次又來興風作浪。然而,當你翻開這本散文以後,卻又覺得事有蹊蹺,書名與內容是嚴重地圖文不符。《來亂》是祁立峰近年來的散文集結,備忘了作者從青春年少到如今已是大學教授、知名作家的諸般心境轉折。字字真情肺腑,絲毫找不到「來亂」的跡象──到底這次祁立峰又在玩什麼把戲?
【來亂的卻不亂來】
聊起《來亂》很難不注意到書名。問及書名的緣起,祁立峰首先就他所觀察到的趨勢談起。他發覺近年來的散文集流行以單一而明確的主題貫穿全書,主題與篇章之間相互補綴,成了部分與整體的緊密關係。然而,因為《來亂》的創作時間跨度極大,五個小輯雖各有主題卻無法以一劃之,祁立峰說:「所以一開始想到的是說,它真的很亂。」後來與妻子討論,妻子建議:「如果你常常出來亂,你就出個來亂。以後如果有人問起你出什麼書,你就說我出來亂的,有一種諧音的好笑。」於是這本散文集的名字,就在看似歪樓的對話中確立下來。
然而,取名為《來亂》絕對不是來亂的,那是面對自我被單一主題化的抵抗策略。此文集收錄了祁立峰近年來所歷所思。曾為文學獎劍客、也是流浪教授,如今已化身文壇知名作家,並任教大學多年。──從這裡到那裡,人生早已闖經各式風景,倘若只取其一來為整體命名,容易有掛一漏萬的危險。主題化有時是種侷限,無法呈現時間在人的身上所按壓的繁複指紋。因此,以「亂」來抵抗分類的暴力,祁立峰所希望保存的是自我的多元面貌。
關於主題化的局限,祁立峰在自序中寫道:「對寫作者來說,主題終究是後設的,是應當被搗亂的。」我們於是就聊起搗亂與寫作者間的關係,他表示這種想法與他研究六朝文學,那時的文學力求新變,因此以中國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就變得相當多元。由於這樣的背景,才讓祁立峰反思:「我覺得即便我們現在講到小說、散文,有一個文類的界限,但這個界限其實是可以混淆的。」《來亂》一書中不乏多篇以小說筆法寫就的作品,多少反映了祁立峰對創作的思考,又頑皮、又認真地掙脫小說與散文的二元框架。祁立峰接著表示:「更進一步說就是主題,你會問我說它有什麼議題?那就變成說我要被歸納,我一定要講到說貴圈的問題、或是九○年代歌曲的記憶,但我覺得它其實就是我這幾年想到的主題,它是沒有連貫性的。」因此,祁立峰說得沒錯,這本散文集確實很亂,不僅亂在體裁的分野、也亂在主題的分散。有道是「亂拳打死老師傅」,但對祁立峰而言,這套亂拳並非毫無章法,它紮紮實實地就是一套拳法。
抗拒因歸納而窄化人所擁有的複雜性,回溯過往,這思維同樣也出現在祁立峰於去年出版的《讀古文撞到鄉民》中。他於該書寫道:「這些古人就如同我們,是一個完整的人。身處暴亂的時代,面對無常的人生,有疑慮或憂患,有任性有妥協。」如今他只是以同樣的態度來處理自己與自己的作品。那些「身存此世的證明」,無論如何歪斜駁亂無以名之,都宛如自我的分靈體,記憶了我們的完整。
【文壇鄉民再進化】
當問起未來的寫作計畫,身為教育者的他,表示仍會持續古文普及教育的推廣。另外也透露,在小說創作上,會朝向類型小說前進。這難道是文壇鄉民的再進化?我們對這轉向感到相當好奇。祁立峰表示,因為發覺純文學的讀者與日俱減,面對這樣的衝擊,總覺得身為作者的他似乎應該做些什麼。他想的其實是如何替文學、替出版業把閱讀的餅做大,因此將目光轉向類型小說。但他也指出:「台灣類型小說的生產線或體制還跟不上日本、甚至是韓國,更不要說歐美。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很漫長的努力空間。但至少從去年一些作品,像是通靈少女、花甲男孩,可以看到國人對自己創造出來、有在地性的文創還是有熱情的。所以我覺得假設我們寫出一本可能只有東野圭吾六成好的小說,台灣人就會願意讀我們自己的作品、或看我們自己故事改編的作品。」
我們也好奇朝類型小說轉向,是否意味著對純文學創作的放棄?祁立峰不這麼認為。他表示,儘管類型小說為了娛樂性很可能割捨掉純文學所力求刨深的問題,卻又並非不可操作。他拿吉田修一與湊佳苗的作品為例,說明類型小說在理想的狀況下,也能擔負起純文學的任務,那裡頭談論的也還是人性的核心。
但話鋒一轉,祁立峰開始揶揄自己果然太有包袱,就算是像《讀古文撞到鄉民》貌似惡搞的詮釋中,也希望能在其中寓以深意;如今有了類型小說的創作計畫,還是不忘文學與教育的職志。然而這就是祁立峰啊,融合大學教授、作家,與鄉民於一身的三位一體。每當他開口,我們都不知道現在到底是教授、作家,還是鄉民,是誰在說話。
過程都順利,惟落筆後發覺有些問題可以再問深一些,然而這就是訪問當下的敏銳度與技巧。有些材料是在落筆後才意識到,不夠多、不夠深,雖然這都可以經過修辭來掩飾,卻是騙不過自己的。未來也許還會接類似的工作,也許不會。然關於技能,還是不可不提醒自己。
* * *
撰寫:陳佑瑋
攝影:YJ
刊登網址:http://www.unitas.me/?p=2126
今年二月,祁立峰出版了他最新散文集《來亂》。書名承襲他一貫的惡趣,彷彿去年那個在茫茫文獻之中尋找我族身影的資深鄉民這次又來興風作浪。然而,當你翻開這本散文以後,卻又覺得事有蹊蹺,書名與內容是嚴重地圖文不符。《來亂》是祁立峰近年來的散文集結,備忘了作者從青春年少到如今已是大學教授、知名作家的諸般心境轉折。字字真情肺腑,絲毫找不到「來亂」的跡象──到底這次祁立峰又在玩什麼把戲?
【來亂的卻不亂來】
聊起《來亂》很難不注意到書名。問及書名的緣起,祁立峰首先就他所觀察到的趨勢談起。他發覺近年來的散文集流行以單一而明確的主題貫穿全書,主題與篇章之間相互補綴,成了部分與整體的緊密關係。然而,因為《來亂》的創作時間跨度極大,五個小輯雖各有主題卻無法以一劃之,祁立峰說:「所以一開始想到的是說,它真的很亂。」後來與妻子討論,妻子建議:「如果你常常出來亂,你就出個來亂。以後如果有人問起你出什麼書,你就說我出來亂的,有一種諧音的好笑。」於是這本散文集的名字,就在看似歪樓的對話中確立下來。
然而,取名為《來亂》絕對不是來亂的,那是面對自我被單一主題化的抵抗策略。此文集收錄了祁立峰近年來所歷所思。曾為文學獎劍客、也是流浪教授,如今已化身文壇知名作家,並任教大學多年。──從這裡到那裡,人生早已闖經各式風景,倘若只取其一來為整體命名,容易有掛一漏萬的危險。主題化有時是種侷限,無法呈現時間在人的身上所按壓的繁複指紋。因此,以「亂」來抵抗分類的暴力,祁立峰所希望保存的是自我的多元面貌。
關於主題化的局限,祁立峰在自序中寫道:「對寫作者來說,主題終究是後設的,是應當被搗亂的。」我們於是就聊起搗亂與寫作者間的關係,他表示這種想法與他研究六朝文學,那時的文學力求新變,因此以中國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就變得相當多元。由於這樣的背景,才讓祁立峰反思:「我覺得即便我們現在講到小說、散文,有一個文類的界限,但這個界限其實是可以混淆的。」《來亂》一書中不乏多篇以小說筆法寫就的作品,多少反映了祁立峰對創作的思考,又頑皮、又認真地掙脫小說與散文的二元框架。祁立峰接著表示:「更進一步說就是主題,你會問我說它有什麼議題?那就變成說我要被歸納,我一定要講到說貴圈的問題、或是九○年代歌曲的記憶,但我覺得它其實就是我這幾年想到的主題,它是沒有連貫性的。」因此,祁立峰說得沒錯,這本散文集確實很亂,不僅亂在體裁的分野、也亂在主題的分散。有道是「亂拳打死老師傅」,但對祁立峰而言,這套亂拳並非毫無章法,它紮紮實實地就是一套拳法。
抗拒因歸納而窄化人所擁有的複雜性,回溯過往,這思維同樣也出現在祁立峰於去年出版的《讀古文撞到鄉民》中。他於該書寫道:「這些古人就如同我們,是一個完整的人。身處暴亂的時代,面對無常的人生,有疑慮或憂患,有任性有妥協。」如今他只是以同樣的態度來處理自己與自己的作品。那些「身存此世的證明」,無論如何歪斜駁亂無以名之,都宛如自我的分靈體,記憶了我們的完整。
【文壇鄉民再進化】
當問起未來的寫作計畫,身為教育者的他,表示仍會持續古文普及教育的推廣。另外也透露,在小說創作上,會朝向類型小說前進。這難道是文壇鄉民的再進化?我們對這轉向感到相當好奇。祁立峰表示,因為發覺純文學的讀者與日俱減,面對這樣的衝擊,總覺得身為作者的他似乎應該做些什麼。他想的其實是如何替文學、替出版業把閱讀的餅做大,因此將目光轉向類型小說。但他也指出:「台灣類型小說的生產線或體制還跟不上日本、甚至是韓國,更不要說歐美。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很漫長的努力空間。但至少從去年一些作品,像是通靈少女、花甲男孩,可以看到國人對自己創造出來、有在地性的文創還是有熱情的。所以我覺得假設我們寫出一本可能只有東野圭吾六成好的小說,台灣人就會願意讀我們自己的作品、或看我們自己故事改編的作品。」
我們也好奇朝類型小說轉向,是否意味著對純文學創作的放棄?祁立峰不這麼認為。他表示,儘管類型小說為了娛樂性很可能割捨掉純文學所力求刨深的問題,卻又並非不可操作。他拿吉田修一與湊佳苗的作品為例,說明類型小說在理想的狀況下,也能擔負起純文學的任務,那裡頭談論的也還是人性的核心。
但話鋒一轉,祁立峰開始揶揄自己果然太有包袱,就算是像《讀古文撞到鄉民》貌似惡搞的詮釋中,也希望能在其中寓以深意;如今有了類型小說的創作計畫,還是不忘文學與教育的職志。然而這就是祁立峰啊,融合大學教授、作家,與鄉民於一身的三位一體。每當他開口,我們都不知道現在到底是教授、作家,還是鄉民,是誰在說話。
Tuesday, April 10, 2018
品牌與人格養成遊戲
講求品牌的時代誕生了經營自我品牌的社群媒體,是很可以想像的事。或者說經營品牌與經營自我如今是以同個道理在運作的,中國夸夸談論的social credit治理也是。
逛個全聯,簡直就像在瀏覽塗鴉牆,每項產品都是一則貼文,嘈嘈雜雜想對你說話。對你說話,就像一個人,而他所力求的是搖身成你的朋友。品牌想做的事情,就是成為你的同溫層,所以用你的語言、你的思考方式,來接觸你。就算是在如今專注力僅能給予不到一秒的資訊核爆時代,也要與你一見鍾情。
branding與寫小說很像,感官成敘事啊。
逛個全聯,簡直就像在瀏覽塗鴉牆,每項產品都是一則貼文,嘈嘈雜雜想對你說話。對你說話,就像一個人,而他所力求的是搖身成你的朋友。品牌想做的事情,就是成為你的同溫層,所以用你的語言、你的思考方式,來接觸你。就算是在如今專注力僅能給予不到一秒的資訊核爆時代,也要與你一見鍾情。
branding與寫小說很像,感官成敘事啊。
Apr. 9, 2018
閨密女友最近想租屋,四處問我們這幾個男同志能不能合住,因為她幻想著廚房與客廳。
閨密:「我一定會在客廳看書,可是我擔心你們男同志老是帶人回來,我就要一直打招呼。」
摸:「好,如果我帶人回去,我就會跟他說,我家不乾淨,人家都說有個女的跟我們一起住但我都看不到,如果你有看到千萬不要跟她打招呼。」
* * *
男友上次從日本帶了著名的月經止痛藥EVE回來。男友:「你頭痛就吃那個啊,一顆、兩顆都可以。」但我還恍惚在自己的疑惑裡,我等了30年的那個,怎麼第一次來就痛頭呢。
(被宮家64掌毆先)
* * *
我爸直到國中前往高雄借居舅公家念書前,都生活在茄萣漁村。以前呢,常有小孩到海邊戲水溺死,我爸就始終被告誡不許到水邊活動。當然在諸多繪影之下,遂有許多傳說,比如不准在陌生的灘 邊喚人家的名字。相關的禁忌也出現在山中,同伴間多稱呼彼此的小名,──畢竟本名有相當強烈的指涉性,像一支羽箭早已擊在特定的靶上那樣。
我兒時很著迷於類似的禁忌,那是因為懼怕,也因為神祕。如今依舊深深迷戀,卻是因為對心理所幻化出來的諸般敘事感到美麗。
無論何種幻夢,饒是恐懼,都是很眩目神迷的。
* * *
男友應徵九州社區營造NPO,今日正式on board。在此之前他已在該處默默協助一年多(而那也是他論文研究的基地),所以工作的同事與內容多不陌生。
問他今早做了什麼,他說沒什麼,牽了兩隻小山羊把牠們栓在有草的地方。聊起山羊與人遊戲的方式就是用頭輕輕地頂人。然而,只是用目測的方式很難曉得原來山羊遊戲時頂人力道並不強,也不曉得那就是山羊的習性,難免心生畏懼。
兩隻山羊一隻不到一歲、一隻一歲半。其中一隻特別暴走,所以對牠施了過肩摔,壓制在地告訴他不許這樣。
好想好想養羊咩咩噢。但男友一定不同意啊他說好臭好臭。
閨密:「我一定會在客廳看書,可是我擔心你們男同志老是帶人回來,我就要一直打招呼。」
摸:「好,如果我帶人回去,我就會跟他說,我家不乾淨,人家都說有個女的跟我們一起住但我都看不到,如果你有看到千萬不要跟她打招呼。」
* * *
男友上次從日本帶了著名的月經止痛藥EVE回來。男友:「你頭痛就吃那個啊,一顆、兩顆都可以。」但我還恍惚在自己的疑惑裡,我等了30年的那個,怎麼第一次來就痛頭呢。
(被宮家64掌毆先)
* * *
我爸直到國中前往高雄借居舅公家念書前,都生活在茄萣漁村。以前呢,常有小孩到海邊戲水溺死,我爸就始終被告誡不許到水邊活動。當然在諸多繪影之下,遂有許多傳說,比如不准在陌生的灘 邊喚人家的名字。相關的禁忌也出現在山中,同伴間多稱呼彼此的小名,──畢竟本名有相當強烈的指涉性,像一支羽箭早已擊在特定的靶上那樣。
我兒時很著迷於類似的禁忌,那是因為懼怕,也因為神祕。如今依舊深深迷戀,卻是因為對心理所幻化出來的諸般敘事感到美麗。
無論何種幻夢,饒是恐懼,都是很眩目神迷的。
* * *
男友應徵九州社區營造NPO,今日正式on board。在此之前他已在該處默默協助一年多(而那也是他論文研究的基地),所以工作的同事與內容多不陌生。
問他今早做了什麼,他說沒什麼,牽了兩隻小山羊把牠們栓在有草的地方。聊起山羊與人遊戲的方式就是用頭輕輕地頂人。然而,只是用目測的方式很難曉得原來山羊遊戲時頂人力道並不強,也不曉得那就是山羊的習性,難免心生畏懼。
兩隻山羊一隻不到一歲、一隻一歲半。其中一隻特別暴走,所以對牠施了過肩摔,壓制在地告訴他不許這樣。
好想好想養羊咩咩噢。但男友一定不同意啊他說好臭好臭。
節奏與創作
創作與某種心理的速度與節奏有關,有時為了名聲速度就亂了調。有時卻是因為生理自身的混淆,大腦內化學物質的經濟,也能紮成亂籐不成器。
下筆前努力在暴風雨臨在的屋裡調整舊式收音機的天線與輪盤,在黑白雜訊放映之中尋找一條可辨識的說話頻道,這就是我需要獨處的重要因素。
獨處是把自己放成一座實驗室,盡可能地控制變因,在其中創造自己。我不曉得過往不明白我為何獨處的人能不能明白這回事,但不明白也無所謂,這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必須選擇的生活方式。
我獨處所需的是自由,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也是自由。
下筆前努力在暴風雨臨在的屋裡調整舊式收音機的天線與輪盤,在黑白雜訊放映之中尋找一條可辨識的說話頻道,這就是我需要獨處的重要因素。
獨處是把自己放成一座實驗室,盡可能地控制變因,在其中創造自己。我不曉得過往不明白我為何獨處的人能不能明白這回事,但不明白也無所謂,這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必須選擇的生活方式。
我獨處所需的是自由,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也是自由。
Tuesday, April 3, 2018
Apr. 3, 2018
我的直覺從來沒有令我失望過,但若曾在人生的歧路上做了錯誤的決斷,往往是因為他人的社會劇本恍如賽倫女妖的歌聲對我吟唱。
我爸曾經在安麗做過內部的高層經理,辦公室相當氣派,在長廊的間中以玻璃隔間,間內有沙發,走出辦公室的廊外有遊戲室、食物不虞匱乏的茶水間。──這是我體內的其中一支賽倫之歌,它影響著我對工作的想像,也插手了我對人生實踐的藍圖。但我內心多少也曉得就算有能,那也不是我希望實現的事業職志。
希臘神話中只有兩位角色安全地通過賽倫女妖的所居之地,一位是奧菲斯,他用自己的豎琴與女妖的歌聲對抗;另一位,則是將自己繩束於船桅的奧德修斯。
前者以才華抵抗賽倫之歌的魅迷,後者以他物的綁縛以防自己雖迷卻不至跳入海中。這兩者都是拒絕的策略。但我希望自己不會只是奧德修斯。
所謂止步並不會帶人抵達。
* * *
前幾天疑惑男朋友從福岡帶回來的木雕為何,今日他揭曉,是九州地區的傳統工藝玩具,叫雉子車。網路上的資訊多半是日語,我懵懵懂懂也只讀懂了它似乎是平家一族逃難後流落此地所做的玩具。
其實就是以鳥為造型的手動噗噗。
* * *
男友提到去上交通講習課,曉得福岡縣的事故發生率是全日本第四名。講師因此調侃地說道:「大家不覺得丟臉嗎?」
日本人不只執著於日本人認同,還很以各縣市人自居。彷彿小組小隊那樣活在彼此的自尊裡,為了榮譽,為了身為各式各樣的「我們」。
讀到資料說,九州人會在店內擺設雉子車。而雉子車是九州特有的工藝物。以某地獨有的事物來作為認同的象徵,這雖然同樣可見於台灣,卻不這麼強烈。這種現象看在我這種沒有地方意識的人的眼裡,就覺得特別有趣。
男友臆測也許以前各地都是國吧。各地風土,各地誌。
* * *
無意間讀到馬翊航寫媽祖,在該文的用圖上,就兩句話:「媽祖行路,海湧因緣。」而我深深被「海湧因緣」這四個字所吸引。
意象清晰,卻又抽象地浪打因緣。很美呢。我在履歷上提到自己最早被修辭的迷魅所吸引,而後終於明白文學與語言的奇術之間有重疊、有分別。我為語言耽美,但也深刻地對這耽美小心翼翼。
畢竟辯術是辯術,哲學是哲學。擁有切分的刀鋒,還是重要的。
我爸曾經在安麗做過內部的高層經理,辦公室相當氣派,在長廊的間中以玻璃隔間,間內有沙發,走出辦公室的廊外有遊戲室、食物不虞匱乏的茶水間。──這是我體內的其中一支賽倫之歌,它影響著我對工作的想像,也插手了我對人生實踐的藍圖。但我內心多少也曉得就算有能,那也不是我希望實現的事業職志。
希臘神話中只有兩位角色安全地通過賽倫女妖的所居之地,一位是奧菲斯,他用自己的豎琴與女妖的歌聲對抗;另一位,則是將自己繩束於船桅的奧德修斯。
前者以才華抵抗賽倫之歌的魅迷,後者以他物的綁縛以防自己雖迷卻不至跳入海中。這兩者都是拒絕的策略。但我希望自己不會只是奧德修斯。
所謂止步並不會帶人抵達。
* * *
前幾天疑惑男朋友從福岡帶回來的木雕為何,今日他揭曉,是九州地區的傳統工藝玩具,叫雉子車。網路上的資訊多半是日語,我懵懵懂懂也只讀懂了它似乎是平家一族逃難後流落此地所做的玩具。
其實就是以鳥為造型的手動噗噗。
* * *
男友提到去上交通講習課,曉得福岡縣的事故發生率是全日本第四名。講師因此調侃地說道:「大家不覺得丟臉嗎?」
日本人不只執著於日本人認同,還很以各縣市人自居。彷彿小組小隊那樣活在彼此的自尊裡,為了榮譽,為了身為各式各樣的「我們」。
讀到資料說,九州人會在店內擺設雉子車。而雉子車是九州特有的工藝物。以某地獨有的事物來作為認同的象徵,這雖然同樣可見於台灣,卻不這麼強烈。這種現象看在我這種沒有地方意識的人的眼裡,就覺得特別有趣。
男友臆測也許以前各地都是國吧。各地風土,各地誌。
* * *
無意間讀到馬翊航寫媽祖,在該文的用圖上,就兩句話:「媽祖行路,海湧因緣。」而我深深被「海湧因緣」這四個字所吸引。
意象清晰,卻又抽象地浪打因緣。很美呢。我在履歷上提到自己最早被修辭的迷魅所吸引,而後終於明白文學與語言的奇術之間有重疊、有分別。我為語言耽美,但也深刻地對這耽美小心翼翼。
畢竟辯術是辯術,哲學是哲學。擁有切分的刀鋒,還是重要的。
Subscribe to:
Posts (Atom)